译者: 子曦

阅读前文——揭开“伊斯兰恐惧症”的面纱 :对话阿亚安·希尔西·阿里 (一)
哈里斯:在此点上你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表明布雷维克的存在是一种糟糕的讽刺。他沉迷于欧洲的伊斯兰问题,但是他的变态行为让那个问题更难以说出来。这个人己成为所有圣战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礼物。
让我们谈谈关于你在荷兰避难的种种误解。
希尔西·阿里:1992 年当我到达荷兰时,我在接纳面谈时假报了我的出生年份。我说我是 1967 出生的,但实际上是 1969 年。我也修改了我祖父的名字。在许多部落型社会中,取代单一姓氏的 是你有一串姓名——我是阿亚安,我父亲是希尔西,我父亲的父亲在出生时被命名为阿里。在此 之后,当他长大成为一名武士时,他被称为马干(索马里语“保护”或“庇护”),因为他保护 了他所征服的一些人。马干本来只是他后来所得的一个绰号。技术上说,我称阿里并没有撒谎, 因为那也曾是他的名字。我是故意这么用的,因为我想,如果我能做这个接纳面谈,那么我的父 亲或他将我嫁给的那个男人也会来,他们会说正在寻找生于1969年11月13日的阿亚安·希尔西·马 干,他们会很容易找到我。我想防止这种情况,所以我称自己为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并将我的 出生年份改为 1967 年。我试图掩盖我的踪迹,只是为了不被立即发现。我以前从来没有在有任何 保护的制度中生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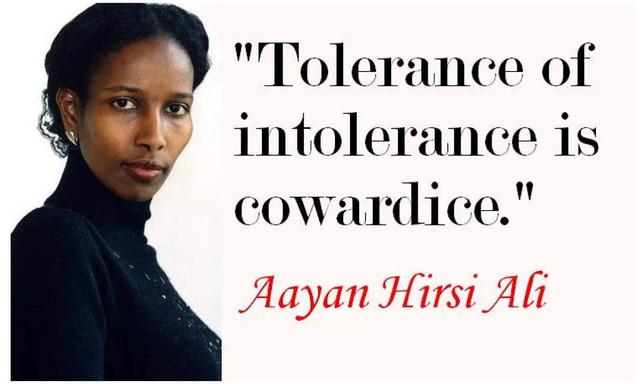
希尔西·阿里的名言:对不宽容的宽容是懦弱
哈里斯:所以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担心有人会来荷兰伤害你?希尔西·阿里:哦,是的,绝对。我担心我的父亲或我们的族人——抑或我被嫁给的那个男人 ——会来搜寻并找到我。他们确实来了!我的前夫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出现在我所在的避难所。但 在那时我己经在这个国家呆了 4 到 6 个月,即使是如此之短的一段时间,我也懂得我拥有的权力。
在他们出现的那天,我去接待中心向一位工作人员坦白了一切。她的名字叫西尔维亚,她说“如果你不愿意,你不必跟他走。你己超过 18 岁。实际上,在荷兰这里,你的婚姻并没被认可,因为 他是加拿大人而婚姻是在别处注册的。所以我们会保护你。我马上叫警察。”就在这时我真正独 立了。我己经自己一个人过了好几个月,我想我能照顾好自己更长的时间。
我不知道事情是否改变了,但当时,如果你要求政治避难,会指定一名法律援助团体成员帮你准 备面试。我告诉我的法律援助律师强制婚姻的事,她说这个申请避难的理由不够充分,我必须拿 出别的东西来。因此,基于她给我的信息,我改编了我的故事。
1992 年索马里内战正酣,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为索马里人提供避难。实际上,在那时只要说 你是索马里人就够了。因此,在我面谈时,我没有说强加给我的婚姻,也未提及在沙特阿拉伯、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经历,我只是假装直接从索马里来的,为逃避内战。
然后,在 2002 年,自由派政党 VVD 问我要不要进入议会以协助有关穆斯林移民的人权问题——我 说好的。作为政党,他们深入访谈了所有可能成为国会议员的人,以确定个人背景中是否有任何 可能产生丑闻的东西。我对他们很诚实,告诉了他们一切。政党的领导人咨询了律师,了解我的 移民细节会有多大问题,律师说,“噢,不,选民会更感兴趣的是她已经这么好地适应于我们的社 会的事实。没有人会在意这个善意的谎言。”
所以,当可以说出真相时,我说出了真相。回到 2002 年时,我不再恐惧。我己经找到了我的路。 我感觉很坚强。我有自己的朋友圈。因此没必要再让谎言继续下去了。从那时起,在我参加的数 百次访谈节目中,我都公开说明了真相——离开索马里之后我曾生活在其它国家,我为了逃离强 制婚姻而来到荷兰。
当移民和归化部长使用我的原始避难申请面谈记录作为剥夺我公民身份的政治工具时,事情演变 成为一桩政治丑闻。政府强制她将公民身份归还给我,那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当她归还我的公 民权时,联合政府中一个小党派的一名成员要求她辞职,否则退出政府。最终这个党派退出了, 政府也随之倒台。我的那部分生活经历也由此上了新闻报道。

索马里
哈里斯:很清楚,你告诉移民官他们需要听到的以确保你自身的安全。你当时正在躲避恐吓你的 人,其原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看不出任何正经的人能拿这个责难你。
希尔西·阿里:他们并未拿这个责难我。它只是一个工具。要使污名化行动有效,你需要材料, 而那是他们使用的其中一个。如果她并非总是完全诚实,那么她关于伊斯兰的言论也是一个谎言。
哈里斯:好像你对伊斯兰的论断很难证实似的。我有时想干脆这样好了,作为一种行为艺术,你 站出来说,“你逮到我了!我说伊斯兰的都是在撒谎。伊斯兰教义下女人与男人完全平等——叛教 或渎神都不是问题。”
希尔西·阿里:是的——还有荣誉谋杀、剥夺女童教育、否定女人不经男性亲属允许就可出门的 权力、给才 9 岁女孩执行童婚、持续以“纯洁”名义实施女性生殖器残割以及对同性恋实施石刑, 那些都只是巧合。
哈里斯:我想谈的最后一个个人问题,是你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从属关系。告诉我你是怎么去 AEI
工作的,以及为什么那对你是合情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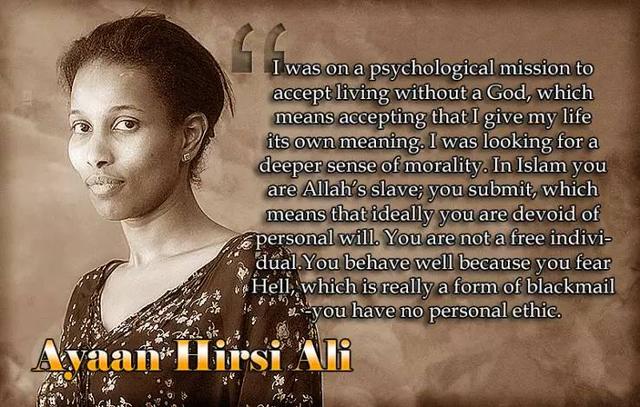
希尔西·阿里:回到 2005 年,我己经知道我不想继续在荷兰国会做第二任期了。在我的第一任
期内,我承诺致力于妇女权益和融合穆斯林入荷兰社会的问题,我觉得再做一任也不会在我己经
做到的程度上有太大改观。在荷兰体制中,你在一任内专注某个问题,而在下一任内转移到别的
方面。但是我不想转移到其它问题上。我不愿以政治作为终身事业。
于是我与辛西娅·施耐德联系,她是比尔·克林顿总统任上的驻荷兰大使。我告诉她我将去纽约,
在写一本书,并问她是否可以引荐我给一些智库,因为我想回到学术领域。我也想要正常的生活,
因为在 2004 和 2005 年,荷兰政府提供的安保让我觉得如坐牢一般。同时伴随的还有可观的坏名
声。狗仔队总跟着我,我没法出门时不被人认出。荷兰是个很小的国家。我想安静地做研究,我
想有安全感。
因此我接触辛西娅,她带我去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约翰斯·霍普金斯、乔治敦——她带我去
了所有这些研究机构,没有一家有兴趣。他们并未当面说,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批评伊斯兰的
言论觉得不快。
然后,就在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之前的最后一天,辛西娅建议我们试试 AEI。我当时似乎还说“我
无法相信你会带我去那。那应该是个右翼团体。”她说“哦,拜托。你们荷兰人对美国有太多成
见。这儿的事情真的跟你想的大不一样。我是克林顿任命的,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克林
顿的好友——诺曼·奥斯汀就在那。所以它并非你所想的那样,它绝对不是宗教组织。”
就这样我们去了 AEI,我们与诺曼·奥恩斯坦和一位名叫科林·褒曼的女士见了面,他们非常热
情。他们马上介绍我给他们的所长,后者建议我们一个月之后再次会晤。我们继续着对话。我谈
了我的工作,他们告诉我他们做的事。这期间我没有收到任何其它联系过的机构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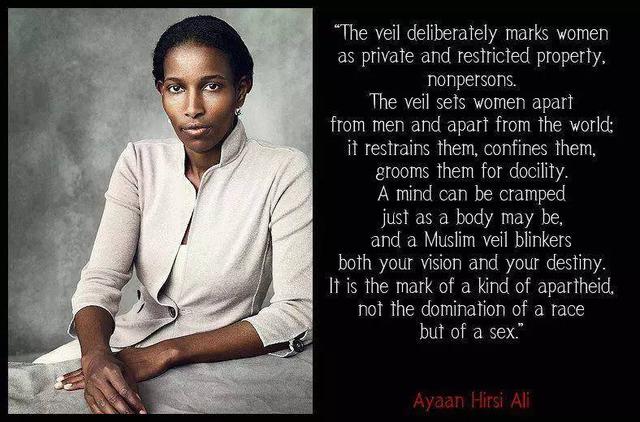
哈里斯:所以对于你为什么会去 AEI 的问题,真正的让人抑郁的答案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没 有自由派的机构为你提供庇护——就在你对自由言论、女权及其它文明规范的全球对话的价值已 清晰展现的时候。而从那以后,你与接纳你的机构的工作关系被用来抹黑你在自由派圈子里的名 声。完美。
希尔西·阿里:嗯,当时确实好像没有其它组织机构愿意象我这样谈论伊斯兰——特别是其对待 女性的方式。
哈里斯:他们现在仍然不会。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道德丑闻。你所受到的对待让我想起在 萨尔曼·拉什迪事件【译注: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英籍印度裔小说家。他 1988 年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撒旦诗篇》引起轩然大波,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以其亵渎先知穆罕 默德和《古兰经》为由下达追杀令。之后拉什迪一直被置于英国警方保护之下,英伊两国甚至一 度断交。该书的各国翻译者与出版者中已有多人遇袭受伤甚至身亡】中许多自由派人士所做的事,他 们责怪他在面对穆斯林社区一触即发的敏感神经时太鲁莽。 几乎在每个测度上我都是自由主义者。给我自由主义价值和偏见的清单,我差不多会在每个框里 打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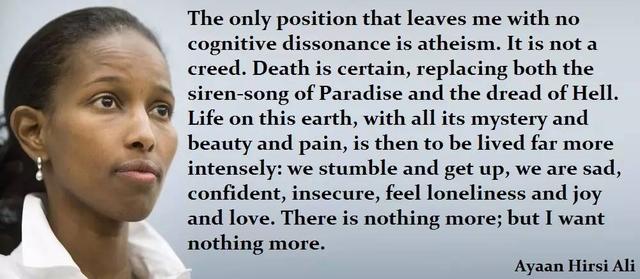
希尔西·阿里:我也会。
哈里斯:但是因为你加入 AEI 的缘故,许多人不知道你是自由派。我记得当荷兰政府取消对你的 人身安全保护时,你的朋友们——我也自豪地位列其中——面临着为你的安保筹款的任务的情景。 如果那时候没有 AEI 的帮助,情况会更糟。因此自由派拿这种工作关系非难你实在可耻。
希尔西·阿里:我为此感到难过。你应该知道的是,在我与 AEI 的所有面谈及其后在那工作的几 年中,他们一直都了解我是一名自由派。机构中没有任何人试图改变我对任何事物的看法——无 论是伊斯兰,还是安乐死、堕胎、宗教、同性恋权益,或者任何其它我的许多同事为之不满的事 情。他们从未压制我的无神论思想或者质询我在公开场合的言论。这是个很棒的研究所。
哈里斯:作为相关的对照,我要讲一下当我为你的安保筹款时,我接触了我在“温和的”穆斯林 团体中的一些联络人。特别地,我联系了礼萨·阿斯兰(Reza Aslan),抱着完全的诚意。我这么 说,“礼萨,如果大多数温和的穆斯林帮助保护阿亚安免受少数极端派所害,这不是很好吗?” 对我来说,我毫不怀疑像礼萨这样争辩伊斯兰只是另一种宗教而已的人,会真正用心确保人们可 以安全地批评甚至抛弃他们的信仰。
但礼萨所做的只是攻击你偏执,并且否认你有值得重视的人身安全问题,无视所有证据。坦白讲, 他的回应令我震惊。我对这种程度的道义失明和恶意没有准备,尤其在我寻求帮助的时候。
希尔西·阿里:事情是这样,山姆。有些温和派穆斯林憎恨我——是的,那是个强烈的字眼,但 我认为他们的言辞支持这一点——因为我让他们感到不安。我说的东西给他们带来无法忍受的不 和谐。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恨我比恨基地组织还多一些。
(待续)






您可以选择一种方式赞助本站
赏